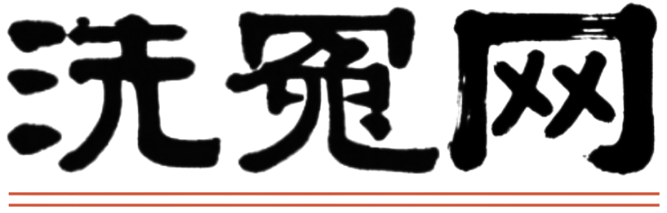在冬天的尽头:金哲红的二十三年

吉林的冬天总是漫长的。风从松花江上吹过,穿过吉林监狱的铁门,带着金属味道的寒气钻进会见室的缝隙里。2015年11月12日,金哲红拄着双拐,走到厚厚的玻璃窗前。他对面的律师正从北京来,带着厚厚的案卷笔记和一腔未熄的坚持。那一年,他已经在狱中度过第20个年头。
“什么时候能有个消息?”他问。
这个问题,他问了无数遍。律师也回答了无数次,每次的答案都一样:“我们还在努力。”
寒冷的冬夜
1995年,一个寒冷的夜晚,吉林市发生一起命案。警方在案发后不久便锁定了金哲红,一个当时32岁的个体商人。然而证据并不充分,甚至可以说贫乏。除了几份在刑讯逼供下形成的“口供”,案件中几乎没有任何物证。
那是一个对“口供”极度依赖的年代。以口供定罪,是冤案的常态。金哲红被迫承认了自己没有犯下的罪。那一年,他被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。
他一直喊冤不认罪,服刑期间也一直喊冤。
在狱中,金哲红写下了数十份申诉信,从吉林中院到最高人民法院,层层寄出。信像雪花一样被退回。十九年间,他的冤屈在档案柜里积成灰。
一封求助信
2013年,“洗冤网”的律师团队收到一封电子邮件。发件人是一位女士,她写道:“吉林有一个重大冤案,请求你们帮助。”
那是金哲红案的又一次呼喊。那一年,团队正在全力推动“陈满案”的平反。面对新的求助,他们几乎没有时间。但他们还是接下了案件,至少,先看一看卷宗。
卷宗被寄到了北京。李金星律师大体看了一遍,心里已经有了判断
“没有物证,没有证人,只有口供。”
这是刑事律师最熟悉、也最警惕的信号。团队立刻达成一致:这是一个重大冤案。

“必须被定罪”的人
2014年,陕西的刑辩律师常玮平第一次飞往长春,前往吉林监狱会见金哲红。那次会见后,他打来一通电话,声音里有压抑的颤抖。
“这个案子,冤得太离谱了,太不可思议了,刑讯逼供太惨烈了,”
刑讯逼供的细节让人难以直视。长时间捆绑、殴打、吊打、电击、睡眠剥夺……金哲红曾多次晕厥,被迫签下认罪笔录。后来他拄着拐杖的腿,就是那段时间留下的伤。
律师在卷宗中发现,除口供外,办案机关并无任何直接证据。作案现场没有指纹,没有脚印,没有目击证人。原审法院三次判决、三次被发回重审,最终仍以口供为核心证据定罪。
在1990年代的中国,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。那时的司法系统正经历市场化初期的阵痛——公检法关系不清,基层政法干部的考核与“破案率”挂钩。一个命案,意味着压力,也意味着政绩。
而金哲红,就是那个“必须被定罪”的人。
不肯放弃的人
2014年夏天,金哲红案正式进入申诉程序,李金星律师组队接力申诉。这个案件包括李金星、袭祥栋、常玮平律师、岳金福律师、吴莉律师、王海军律师、石伏龙律师、黄佳徳律师、任星辉律师在内先后十几名律师代理申诉。
前方会见。勘察现场,当面陈情,向媒体寻求帮助,律师团队始终紧密合作,协作战斗。大家在微信群里讨论策略,在北京、沈阳、长春之间往返。五年间,他们共寄出上千封信。

有一次,李金星律师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门口被拒之门外,他几乎崩溃,对接待法警说:“见不到法官我就不走。”
法官最终走出来,先是批评律师“扰乱秩序”,后来又沉默片刻,说了一句:“这个案子,我们都很重视。”那是律师们第一次听到来自最高法院最直接也最委婉的答复。

最高院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张能宝、胡云腾成为案件转折的关键。法官要求吉林高院重新审查。律师团队提交了厚厚的申诉材料,连同一份光盘——里面是他们把上百本卷宗一字一句数字化的成果。法官看完后说:“见过的最认真的律师。”

漫长的等待
从2016年到2018年,金哲红案再次陷入沉寂。吉林高院的负责人调离,案件无人负责。金哲红的身体每况愈下,他很担心自己怕等不到那一天。
2018年11月30日,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告:金哲红无罪。
宣判那天,金哲红拄着拐杖,站在被告席上。向检察员和法官表示感谢。金哲红说,他没有杀人,认为只要活着,就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那天的阳光正好,从法院大楼的玻璃上反射下来,照在他那张疲惫、苍白的脸上。

冬天的尽头
2019年,国家赔偿程序完成。金哲红获赔468万元。律师们收到了他的信,信纸上只有一句话:
“我终于看见了阳光。”
他们知道,那阳光并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。
毁灭一个人,就是毁灭一个世界;拯救一个人,也是重建一个世界。
金哲红案的平反,不仅属于一个被冤二十三年的个体,也属于那些在制度缝隙中坚持不放弃的人。
在冬天的尽头,有人还在等待春天。